

百草枯是全球第二大除草剂,它的诞生和广泛应用推动了世界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尤其使免耕技术成为可能。1984年,百草枯正式进入中国市场;21世纪,百草枯在中国全面投产,并形成了完备的产业链。
然而,百草枯在中国的发展一波三折。2012年,1745号公告对百草枯工业形成重创。余波未了,一波又起。百草枯毒性级别修订为剧毒,无疑让百草枯行业雪上加霜。因百草枯的安全问题尚未有效解决,农业部暂停受理百草枯产品的登记,这或将为百草枯在中国市场彻底划上句号。百草枯,命悬一线。
百草枯的多舛命运,让百草枯及其整个产业链风雨飘摇。
2015年10月29日,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在上海由由酒店召开了“百草枯发展论坛”。会议邀请了业界相关专家,把脉百草枯面临的困境,全面评估百草枯的发展未来,力求为百草枯觅得生机,为受牵连的百草枯上游产品指点新的发展方向。百草枯,似乎会有生的希望。
本次论坛由中国农药工业协会齐武主任担纲主持。


百草枯上游产品不必"死盯"百草枯
吡啶是百草枯的上游产品,目前,它与百草枯的命运息息相关。上海市农药研究所张一宾教授通过其精彩演讲,希望开拓农药行业对吡啶的发展思路。
据张教授介绍,目前吡啶的全球产能为18万~20万吨,产量约12万吨。主要用于农药、饲料添加剂、医药和涂料等领域。其中,农药是吡啶的消耗大户。吡啶是生产百草枯、毒死蜱、敌草快等的重要原料,尤其是生产百草枯需用吡啶6万~7万吨,也即,吡啶约一半的市场流向了百草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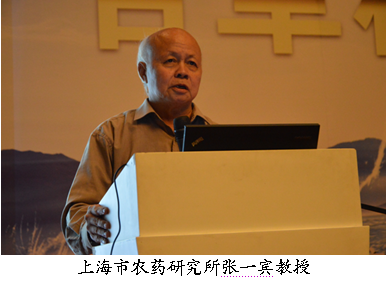
一旦百草枯在中国遭禁,吡啶的出路在哪里?张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做好百草枯的剂型产品,更多地开辟国际市场;努力开发吡啶衍生物,尤其是3-甲基吡啶,此关键中间体在农药中的用途最广;以吡啶或其衍生物为原料,开发现有农药的新路线,如拜耳以3-甲基吡啶为原料生产吡虫啉,国内也可以在这条路线上多下功夫等。
报告中,张教授还列举了50多个以吡啶及其衍生物为原料可以合成的农药,其中不乏大咖级产品。吡啶完全可以不再“死盯”百草枯,而是应该打开视野,寻找更多下游目标产品,或许新的利润增长点并不逊色于百草枯。如杀虫剂中的氯虫苯甲酰胺、溴氰虫酰胺、啶虫脒、烯啶虫胺、吡蚜酮等,除草剂中的敌草快、烟嘧磺隆、砜嘧磺隆、吡氟甲禾灵、炔草酯等,杀菌剂中的啶氧菌酯、啶酰菌胺、氟吡菌胺、氟吡菌酰胺等。
新的含吡啶基的农药依然是当今农药开发的热点,在此背景下,吡啶的未来市场前景仍可乐观。不过,张教授强调,目前吡啶的产能已经过剩,新建、扩建需慎思而后行。
爱子心切,"百草枯之父"艰辛研发安全剂型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李德军团队研究百草枯安全剂型时的心路历程。
通过“熔融喷雾冷却结晶造粒”,成功生产无粉尘百草枯可溶粒剂,生产的产品完全达到商品化要求。该成果获得了4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并申请了国际专利。
在论坛上,被誉为“百草枯之父”的山东省农药科学研究院李德军院长为与会代表带来了“百草枯水溶性粒剂研发与生产”的激情洋溢的报告。大家对李院长们的艰辛付出肃然起敬。4年多的日日夜夜,非亲历亲为者,无法体会期间的煎熬。

无粉尘百草枯可溶粒剂,是一种坚硬的结晶体,更是智慧、毅力和血汗的结晶,它代表着中国农药研究的水平,它或将为百草枯迎来一线生机。
如果服食百草枯“有药可治”,那么百草枯几乎是农药产业的杰出典范。无论是生产过程中的绿色清洁化、产业链的循环经济,还是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百草枯都无可挑剔。
然而,农业生产上广泛使用的百草枯水剂,却将百草枯唯一的、致命的缺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最终导致百草枯落入今天的境地,命悬一线。
爱“子”心切的“百草枯之父”,率领他的研究团队,走上了一条探索百草枯安全剂型的艰辛之路。李院长认为,有效规避百草枯致命弱点的颗粒剂,是比水剂更好的剂型。然而百草枯吸入毒性极高,解决生产和应用过程中的粉尘问题谈何容易。车间及排风口粉尘浓度控制标准为0.01毫克/立方米、百草枯固体制剂粉尘标准最大为0.0033%(重力法),这两项严苛的指标几乎成为百草枯颗粒剂生产不可逾越的障碍。
常规造粒法无法实现全密闭、连续化生产,李院长他们最终发现的“熔融喷雾冷却结晶造粒”是为百草枯颗粒剂量身打造的生产技术,是造粒技术的重大突破,目前还没有发现其他农药可以采取这种方法成功造粒。
从原料加入到袋装成品出产,整个过程始终处于伴水湿润状态,循环风系统和物料系统全密闭循环,全密闭连续运行,无人工倒料和间歇出料环节,不存在与大气环境换气、排空和暴露接触的工艺节点,不存在粉碎、干燥、筛分、粉尘捕集处理、旋风分离、水膜除尘、过滤、更换除尘布袋等操作,不产生废水、废气。生产的百草枯可溶粒剂是具有良好流动性的结实的圆形或椭圆形固体颗粒,粒径在20~80目之间。经检测其有效成分含量为20%~50%,水分含量10.5%~13.5%,各项质量指标完全合格,经MT-171方法检测,产品粉尘含量为几乎无粉尘(检不出)。
实现无粉尘,似乎是天方夜谭,然而李院长他们做到了,这是因为百草枯可以形成三水合结晶体。但仅仅是三水合结晶体还无法解决储存、运输过程中因高温失水而产生粉尘的问题。研究人员通过添加助剂及改变结晶条件来改造百草枯晶体结构,最终形成了不同于百草枯、有别于百草枯三水合物的新的分子结构,从而达到了锁住水分的目的。热重分析表明,67℃时,失水为0.75%;120℃时,失水为5%。
李院长介绍道,百草枯独特的生产工艺决定了其无粉尘产生。脱水和混料工段百草枯存在于液相中,不产生粉尘。喷雾冷却造粒时在密闭喷雾造粒塔中进行,塔内系统循环风处于全密闭状态,无工艺尾气排放口。产品自始至终是在水的捆绑和陪伴下,产品与水在分子水平上结合,最终产品颗粒中仍牢固含有10%以上的水分,从源头上避免了粉尘产生。
同时,生产时塔内压力略低于常压,确保无粉尘外溢。百草枯颗粒剂双袋包装机密封良好,微负压条件下运转。双袋包装机外空间密闭,微负压条件运行确保操作环境安全。
因此,“熔融喷雾冷却结晶造粒”从根本上解决了百草枯生产时粉尘溢出对操作人员的职业健康危害这一世界性难题,使粒剂生产规模化、安全化、连续化、密闭循环化、低耗清洁化成为可能。
另外,李院长用详实的数据告诉我们,生产百草枯可溶粒剂与水剂的成本基本相当。他说:“生产50%百草枯可溶粒剂吨成本为35,295元,18.5%百草枯水剂吨成本为13,579元。以折百计算,生产1吨折百百草枯粒剂成本为70,590元,1吨折百百草枯水剂成本为73,400元,两者成本基本相当,可溶粒剂略有优势。”
李院长总结道,经过4年多顽固、偏执的艰辛攻关,可以断言,百草枯水溶性造粒技术已经取得关键性突破,经过500吨/年中试装置连续运转,安全可靠,清洁低耗,产品运输储存使用皆可满足要求,生产成本与水剂基本相当,产品经水溶性袋包装,消除了消费者与药物的接触机会,可以有效避免冲动性自杀者服食。
百草枯可溶胶剂是水剂的重要替代产品
1745号公告给百草枯水剂明确了禁用日期。水剂大限在即,替代的非水剂型获准登记的有可溶胶剂和可溶粒剂,而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20%百草枯可溶胶剂是迄今唯一“三证”齐全的产品。该公司刘奎涛经理在论坛上对该产品作了详细介绍。

2010年9月,红太阳开始研发百草枯可溶胶剂;2013年9月,其20%百草枯可溶胶剂获准正式登记;2014年9月,该产品获得生产批准证书;2015年1月,“三证”齐全的20%百草枯可溶胶剂正式生产,并投放全国市场,成为百草枯水剂的重要替代产品。
20%百草枯可溶胶剂因无飞溅伤害风险、无粉尘隐患、流动性低、可吞咽难度大,而大大提高了安全性。该产品采用推杆式罐式包装,药液残留低。同时,红太阳实施了包装回收政策,“谁销售,谁回收”,并集中焚烧处理,从而确保安全环保。
据刘经理介绍,20%百草枯可溶胶剂加工工艺简单,其生产设备与水剂类似,仅在混合釜上增设了加热装置,完全可实现规模化、清洁化生产。目前,红太阳现有装置全负荷生产,可日产20吨、年产6,000吨以上的百草枯可溶胶剂。
目前,红太阳正加紧新建2套大容量加工装置,以及2条更高效的全自动分装线,计划2016年初投入使用,预计将实现产能2万吨/年。同时,2016年起,公司将启用新一代推杆式胶管作为可溶胶剂的专用包装瓶,全面提高产品质量与分装效率,并进一步提升其使用安全性和方便性。
20%百草枯可溶胶剂自年初投放市场以来,产品已覆盖全国19个省(市)或地区。在产品推广过程中,公司进行了大量的试验示范工作。20%百草枯可溶胶剂快速触杀,性能突出,使用时推荐二次稀释。可广泛用于荒地除草、田埂除草、果园除草以及恶性杂草(如小飞蓬、藜)的防除等,防效优异,对牛筋草、葎草、大巢菜和小飞蓬等的防效甚至达到100%。
不过,刘经理也坦言,在水剂没有彻底退市之前,百草枯可溶胶剂很难打开局面;同时废弃包装物的回收与处理也增加了产品成本,降低了产品的竞争优势。
南京高正首家引进国际先进喷雾干燥流动造粒技术装备
南京高正农用化工有限公司是我国首家引进国际最先进喷雾干燥流动造粒技术的公司。该技术装置具有全封闭、自动化、连续化、清洁化造粒,粒径可控,粒质强度好等优点,可年产1,000吨百草枯可溶粒剂。其工艺设备居国际领先水平,不仅填补了百草枯可溶粒剂制备工艺的空白,而且将农药行业液体造粒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高正农化董事长汪茂勤在论坛上作了题为“60%百草枯可溶粒剂工业化探索”的报告,全面阐述了这项技术及工艺装备。

据汪董事长介绍,高正农化于2011年立项,2012年从国外进口设备完成中试。2013年,公司投资1,200万元,从发达国家引进国际最先进的自动化液体喷雾干燥流动造粒技术装备,这在国内尚属首例。2014年6月,公司完成了整套生产装置的安装与调试;7月进入试生产。
截至目前,高正农化已生产了近400吨60%百草枯可溶粒剂,并投放国内外市场,是迄今生产百草枯粒剂产量最高的公司。整个生产流程无粉尘外泄,各项指标均达到标准要求。
汪董事长告诉我们,该装置由百草枯混合液输送系统、四级热风系统、加压二流体雾化系统、一次干燥造粒系统、一级除尘细粉返塔系统、塔内流动层二次干燥造粒系统、塔外流化床三次干燥冷却系统、二级除尘细粉返塔系统、产品负压收集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以及自动清洗系统等11个部分组成。
他通过幻灯片,翻过一张张照片,让我们直观感受到先进装备的高大上。整洁的厂房,洁净明亮的设备,非常美观,似乎与农药生产全无关联。正如汪董事长所言,他们想把这个项目打造为精致的艺术品。确实,这套“艺术品”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同行的关注,他们纷纷来厂参观,并给予了高度评价,甚至成为业界学习的典范。目前,高正农化百草枯可溶粒剂是获得工信部生产批准证书的国内仅有的3家公司之一。
据汪董事长介绍,这套装置不仅可用于百草枯可溶粒剂造粒,而且适用于所有农药液体喷雾造粒。
草铵膦真能替代百草枯?看企业当家人如何精打细算选品种
“哪家百草枯企业爆炸过?哪家草铵膦企业没爆炸过?”
山东绿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焱的两个设问句在“百草枯发展论坛”上震耳发聩,耐人深思。
显然,这不是从业30多年、作为企业当家人赵董事长选择品种的唯一标准。“安全”是确定品种的首选要素,同时还需要其他大量数据来支撑。
“百草枯与草铵膦、敌草快产品生产技术比较”是赵董事长给会议带来的报告,他从这3个品种的生产路线、合成收率、“三废”、能耗、投资、使用成本等众多方面进行剖析,让数据说话,告诉我们他为什么选择百草枯,为什么至今没敢做草铵膦。

以吡啶和氯甲烷为原料,经3步反应合成百草枯,总收率超过90%。该工艺已经非常成熟。生产1吨百草枯产生浓废水2.5吨,稀废水1.0吨。废水中含氯化钠或氯化铵0.8吨。
目前,全国有10家企业生产百草枯,总产能约7万吨,年产量6万多吨。
敌草快是百草枯的小兄弟,国内以2-氯吡啶为起始原料,经催化偶联和成盐反应两步合成。反应总收率在86%以上。吨产品产生废水2.0吨,氯化锌废渣0.6吨。先正达也生产敌草快,但其合成路线与中国不同。
目前,国内有3家企业生产敌草快,实际产能约3,000吨,年产量不超过2,000吨。
草铵膦是目前国内炙手可热的品种,已建和在建的企业约20家,还有很多厂家跃跃欲试。
国内草铵膦合成主要采用格氏-斯特雷克法,以亚磷酸三乙酯和三氯化磷为起始原料,经格氏、歧化、偶联、加成、氨基腈、水解、精制、氨化等至少8步反应制得草铵膦。总收率为39%~42%。草铵膦的第1步格氏反应,易燃易爆,生产操作中需要绝水绝氧。
草铵膦整条工艺废水产生量约60 t/t产品,大部分废水需要蒸干出废渣,部分废渣、结晶脚料难以再次利用。据悉,有的厂家经过工艺改进后,废水量可降至30~40 t/t产品。
而拜耳公司的合成路线与国内截然不同,其以甲基二氯化膦为原料,经3步反应合成草铵膦。全部工序连续化作业,自动化程度高,总收率在92%以上。无溶剂、无气味,几乎无废渣排放;氨化和水解后的水相可回收套用,是对环境友好的洁净工艺。
赵董事长还从毒性、使用成本、投资成本、环保及配套等方面对3个品种进行了详细比较。
他说,目前草铵膦的使用成本是百草枯的5.5倍,敌草快是百草枯的3.2倍。从投资成本来看,草铵膦是百草枯的7倍,敌草快是百草枯的2倍。
他认为,目前国内草铵膦生产工艺还相当不成熟,而拜耳路线技术含量很高,需要组织攻关。
从收率看,草铵膦仅40%的总收率,而百草枯为90%,收率越低,“三废”越高。草铵膦吨产品的废水量约为45吨,百草枯为3.5吨;草铵膦的废渣量为3.6吨,百草枯为0.8吨;草铵膦的酸碱量为7.0吨,百草枯为1.0吨……
无论从生产成本、生产工艺、“三废”,还是从生产安全、投资回报率来看,相对于百草枯,草铵膦都不成熟。赵董事长强调,如果在此情况下,强行禁用百草枯,上马草铵膦,是极不负责任的。诚然,百草枯吸入毒性很大,误服后无特效解毒药,如果仅以此为由禁用百草枯,也是极不负责的。因为草铵膦的安全风险比百草枯大得多,于是才有了拥有丰富生产经验的赵董事长的振臂一问:
“哪家百草枯企业爆炸过?哪家草铵膦企业没爆炸过?草铵膦大量的废水、废渣往哪里放?”
绿霸“盯着”草铵膦很多年了,也具备生产草铵膦的基础,但赵董事长说:“我至今没敢上。”
赵董事长认为,要选择一个品种,应该全面分析,认真研判。他说:“我们需要组织攻关,把草铵膦的生产工艺攻下来,再把百草枯停下来。”
百草枯在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登记和使用
早在1955年,研究人员就发现了百草枯的除草活性;1962年,ICI(现先正达)公司将百草枯投放市场。2014年,先正达百草枯的全球销售额为6.05亿美元,同比增长8.0%,在公司最畅销产品排行榜中位居第五。
关于百草枯,先正达公司应该具备发言权。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作物方案经理蒋代清在论坛上与大家分享了“全球百草枯应用情况”的报告。从全球来看,百草枯依然是一个利好大于利空的产品。

据蒋经理介绍,截至2015年9月,全球有近90个国家或地区登记和销售百草枯,其中不乏一些法规系统严格的农业市场,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等。有些国家原先已经取消了百草枯的使用,但因为农业生产的需要,又重新启用。由此可见,百草枯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除草剂之一。
为了把百草枯用得更好,一些国家采取了特殊的管理措施。如澳大利亚/新西兰要求,对包括百草枯在内的所有高毒农药必须单独上锁存放;哥伦比亚要求操作人员佩带呼吸面具;日本要求购买者必须签字,申明销售和使用的严格限制;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巴拉圭等则限制百草枯的最高含量;而在美国和加拿大,百草枯仅限用于通过认证的使用者。
百草枯已在全球使用50多年,成为世界最有效、环境友好的除草剂之一,在农业免耕技术的推广、防止土壤流失、有效抗击草甘膦抗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全球5亿种植者中,约有7,500万种植者使用百草枯。其中,约45%的使用者为小农户;约60%的百草枯在亚太地区使用,是亚太市场最重要的单品。
作为百草枯的原创公司,先正达积极采取措施。公司参与制定FAO关于百草枯制剂的标准,明确百草枯水剂中要加入明亮的蓝色染料、强烈的恶臭和催吐剂;公司还与当地非政府组织和自杀预防专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确保农户安全存储产品……
百草枯是被谈叙颇多、褒贬兼备的农药品种。为了让大家更多地了解百草枯,蒋经理向大家推荐了“百草枯信息中心www.paraquat.com”,这是一个非品牌的、开放的、实际且实用的网站平台,目前平台已通过8种语言来传播百草枯的相关信息,以客观、合理、公平地还原百草枯的真实面目。
无论是先正达,还是国内的百草枯生产企业,甚至包括百草枯的广大用户,都希望能在中国市场留住百草枯,所以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用好该产品,努力避免意外摄入,减少蓄意自伤发生率。
禁用百草枯,困惑农业生产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范志伟博士、研究员在论坛上介绍了“百草枯在农林业中的应用”。他说,百草枯为灭生性除草剂,具有触杀作用,斩草不除根。该产品速效,耐雨水冲刷。性价比高达1∶49,迄今,还没有一种农药能超过它。它对环境友好,对后茬安全,其技术和产业已很成熟。

1963年,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橡胶园试验百草枯和茅草枯除草;1978年,黑龙江省农垦系统首次从英国批量进口百草枯。1984年,我国开始大面积推广应用。2014年,百草枯(20%水剂)使用量为10万~12万吨,使用面积2亿~4亿亩次。
范博士介绍道,百草枯在我国农业上的应用非常广泛,主要包括:行间除草、免耕除草、换茬除草、收获后清园、播后苗前除草、果园及林地除草、水生杂草防除、催枯催熟、非耕地除草等。使用百草枯,可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百草枯已在我国应用了30多年,各地已形成了基于使用百草枯的各种生产制度和种植模式。一旦禁用百草枯,可能会造成农民不会种庄稼的混乱状况,而且涉及面很广。杂草猖獗、复种指数降低、耕地撂荒以及药害增加等将使农业减产减收。如果使用更加昂贵的除草剂,使用人工或机械除草,还会增加农业生产成本。另外,我国农业对百草枯有很强的依赖性,在理想替代品尚未出现并大量推广之前,农民对百草枯的刚性需求依然存在。从而形成市场需求和农药管理的矛盾,一些不法分子势必转入地下生产销售,给监管带来困难。
百草枯中毒治愈率显著提高
百草枯吸入毒性高,一旦中毒无特效治疗药,这是阻碍百草枯发展的致命之伤,国内关于百草枯的一系列管理措施出台,也正是基于此。
王海石教授是山东省立医院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医师,他积累了丰富的百草枯中毒救治经验,他为“论坛”带来了“百草枯中毒救治现状与展望”的报告。

据王教授介绍,10年前发生百草枯中毒,国内平均救治成功率仅为20%~30%,每年有数以千计的百草枯中毒病人死亡。只有条件比较好的医院才有较低的救治成功率。
针对这种情况,10余年来,先正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投入了不少人力、物力进行百草枯中毒的防治工作。2011年7月,国内百草枯主要生产企业在中国农药工业协会的领导下,组织成立了“百草枯社会责任关怀工作组”,也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开展农民培训、医生培训等,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据王教授介绍,随着人们对百草枯毒理的认知不断深入,新技术新方法的治疗不断改善,百草枯中毒治愈率显著提升,目前全国救治成功率已达50%~60%。如果进一步加强科研,加强医生培训,几年后救治成功率有望达到70%以上。
“百草枯发展论坛”将平台完全奉献给了命悬一线的百草枯。各路专家纷纷登台,他们都奔向同一个目标,把百草枯留在中国市场。
百草枯中毒救治分秒必争,同样,要挽救百草枯的生命也是分秒必争。“论坛”传递出强烈的信息:从百草枯的科研、生产、应用,到百草枯的中毒救治,相关专家和工作人员都在尽最大努力,来确保百草枯的安全,降低百草枯的风险,希望管理部门能全面考虑百草枯的性能,对百草枯作出公平、合理的评判。

农药快讯, 2015 (22): 23-27.